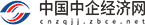【资料图】
【资料图】
道教戏剧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丰富的表现力。除了前面说到的道曲、吟表、科范外,最为一般民众欢迎的,还有具有神秘力量的彩和打,彩如火彩,是魔术一类;打则是包括武术、杂技等内容。道教的丰富表现力,来源于他们修炼的童子功。正一道道士从小学习各种艺术,同时也学习武术等,几乎和戏曲科班无异。不同者是道士因为秉持精神信仰,其学习往往更加虔诚,追求精进。 道教戏剧中,有很多惊人的绝活,有一些涉及障眼法或巫术的内容,比如上刀梯、走火海,还有一些奇异的火彩、魔术、杂技等等。有研究者指出,道教戏剧有点类似汉代百戏,和一般戏文主要敷演一个故事不同,道教戏剧集中展示各种艺术形式,以营造严肃的宗教氛围。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除了营造严肃的氛围,突出仪式性,还有显耀道士本领的意味。如果说世俗戏文,是感人动人为目标;道教戏剧是要让人信服,以征服人心为目标,当然征服人心也需要感人、动人。道教戏剧的动力,也有现实功利的原因。在道教体系中,道士要获得更高职务,就必须在艺术上有所建树。而对于一般观众而言,欣赏道教戏剧多元化的表演,可谓是极高的艺术享受。在文化活动贫乏的古代,道教戏剧兼具庙会、百戏、慈善等一系列社会功能,吸引了各类人群。 道教法事,在观赏者看来,已经类似于看戏。而法事仪式中戏剧成分渐渐独立出来,成为纯粹的戏剧艺术形态。如安徽洪山戏,江苏香火戏,湖南师道戏,都是纯粹的道教戏剧。此外还有安徽的师公戏。道教戏剧因为某种神秘性,往往和傩戏等原始戏剧合流,顽强存续于民间。为了在民间的生存,也和世俗戏剧产生某些交集。因此有的道教戏剧如果不仔细辨别,往往会被认为是地方小戏或傩戏、祭祀剧。 现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道教戏,有福建龙岩的道士戏。龙岩道士戏成熟时间较晚,距今三百多年。 一:行当脚色与剧目 福建道士戏行当简单原始,生旦净丑,与早期南戏类似。生,俊办;旦,女妆;净角为花脸,丑白胡子。道士戏的剧目分文戏和武戏,《瞎子算命》、《收狗精》、《收老鼠精》等等。演出的都是道教相关的故事,以及降妖除魔、劝人入道之类的情节。此外,有条件的,也会演出大戏,如《大收妖》、《目连救母》。降魔除妖是民间对道士的普遍职责期待,道士戏反复出现的王母娘娘和刘海青,寄托了民间的素朴信仰。 二:音乐与表演 道士戏唱腔简单,没有丝竹管弦伴奏,只有锣鼓,类似于今天的川剧高腔。道士戏因为情节限制,往往并不能真正照搬大套的道曲,转而以民歌小调为主要音乐元素,比如《四时景》、《香花景》。道士戏的伴奏是很粗犷的,主要是锣鼓。吹打曲牌比较简单,《将军令》、《朝天子》等等。 道士戏的表演,没有较为苛刻严密的程式,有一些道教科范内容。总体表演比较随意。值得注意的是,道具一词,可能出自道士戏。道士戏专门制作了为演出而设的工具,称为道具。而道具又源于道教法器。道教武戏,常常真刀真枪,尤其是《上刀山》等戏,神秘惊悚,让人过目难忘。道教戏的表演,整体较为随意,一般由具有亲缘关系的父子兄弟同台,规模不大。大戏《目连救母》等,也有系统排练,且需要征集大量群众演员,是一项全民动员的文化活动。道教在明清之际衰微,道教戏却依然很受欢迎。因为道士戏已经从说教,向世俗化、娱乐化过度,且戏剧性不断增强。民间观剧的兴趣重心,已经从聆听教义变成了单纯的娱乐。闹热行的道教戏剧,和民众狂欢的心理期待不谋而合。一如鲁迅先生在《社戏》中恋恋不忘的翻跟斗的戏码。 道士戏在艺术上具有两个特别之处:神秘性和传奇性。其中,对于道教人物的神秘化和戏剧化,是一个重要途径。刘海得道成仙,是一般民众可以期待或触摸的解脱之道。可以说,这是一种触摸可及的宗教艺术形态。道士戏对地方戏影响很大,比如花鼓戏、竹马、采茶戏都有道教戏的某些艺术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