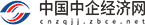(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摘要: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制度逻辑已经指明了转型的理论方向,而转型中出现的种种现实困境,恰恰又标明了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方位。因此,有效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就要以数字化转型逻辑为方向依循,以数字化转型困境为突破重点,构建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多重路径。(一)基础保障:精准识别各类内外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与服务供给职业教育系统的有序运行和良性发展建立在与外部系统不间断的资源交换之上;职业学校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其功能的实现也需要相应的资源支持;职业教育中的个体也有着各自相异的、不断变化的资源需求。可见,资源是职业教育存续和发展的基础保障,而有效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合理高效的配置与供给使得有限的资源达到效用的最大化,从而最大限度支持职业教育转型发展。在这一方面,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服务逻辑提供了有力指引——服务逻辑强调,资源向价值转化的关键在于资源与需求达成匹配,让最需要的人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最合适的资源,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价值。这在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中是难以实现的,而职业教育的数字化则为服务逻辑的实现提供了技术前提。在职业院校内部,教学资源、后勤资源、技术资源、资金资源、人力资源等,都可以借助数字技术进行优化配置和适需供给。首先,要建立统一的数字化资源平台,将学校的各类资源整合接入资源平台,以数据为纽带将校内资源连接贯通,实现资源的网络化统一管理与配置;其次,建立可在多种设备上使用的交互客户端,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向平台提交自己的需求信息;最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开发算法模型,根据用户需求特征精准匹配相应的资源,将需求信息作为订单发送给相应的供应部门,从而完成快速、精准、个性化的服务供给;此外,数字化资源平台可以将资源配置整体情况向管理者可视化呈现,相关数据可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在职业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中,数字化转型同样能够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方面,职业教育承担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职能,这主要以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实现;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在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56]。加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以及深化职业教育与产业、企业的融合共生程度,是推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方面。“互联网+职业教育”大平台是将职业教育资源产出信息与社会需求信息进行整合的互联网平台,通过该平台能够形成“中台”式服务新模式,职业教育与社会之间可以实现高效的数据流动,各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信息可以即时发布到职业教育大平台,职业院校可根据平台大数据科学制订本校未来数年的人才培养计划,并根据市场反馈,在培养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培养内容和方法。同时,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同接入平台,学校可以选择岗位类型匹配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获取优质、适合的实习条件,企业也可以主动发起合作,通过订单式培养、联合技术攻关、实习项目等形式获取学校的人才与技术资源。借助数字技术,职业教育与市场可以在信息充分公开、数据即时交换的基础上,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结构性、摩擦性资源低效配置,从而最大化发挥职业教育的效能。(二)关键环节:以人为本统筹空间建设,创新应用数字化教育场域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将深刻改变职业教育参与者的活动方式,其区别于传统职业教育的最显著特征是职业教育活动将超越物理空间的局限,向虚拟空间不断延展,这种虚实跨界的特性将赋予职业教育以新的生机。然而,职业教育所面临的虚实分离困境已经充分说明:尽管虚拟空间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要使其真正发挥教育价值,就需要超越技术思维,探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虚拟空间的定位、建设、应用与调适,从而使之真正有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明确职业教育数字化空间的理念定位。职业教育的本质是“技艺授受”[57],由此来看,职业教育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仍然是人的发展,这也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根本规定性。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要以人的发展为根本价值,这就为数字化空间明确了定位:职业教育数字化空间是职业教育主体发展的场域。也就是说,空间的拓展和变革,要服务于职业教育主体的发展,而人的发展,无论是技艺的发展、知识的发展还是人格的发展,都有赖于个体与人和物的交互,数字化空间为这种交互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其次,系统规划、统筹推进空间建设。要着眼于职业教育数字化整体空间进行系统性规划设计,制订职业教育数字化空间建设蓝图,注重构建合理规划、虚实一体、互联互通的职业教育混合空间。要通过广泛布局交互环境和拓展交互设备,使现实与虚拟空间的切换便捷化、泛在化、无缝化;要通过统一端口、协议与平台,做到学校各项业务在同一网络环境下进行,实现虚拟空间的一体、互联;要加强数字基建,不断提升无线网络覆盖率、增加互联网出口带宽、扩大本地数据中心、购买云服务、建设多媒体和虚拟仿真实训教室,为优化主体在虚实混合世界的生存体验提供强大的环境保障。再次,要开发适应虚拟空间的教育活动方式。虚拟空间的交往具有不同于现实空间的独特性,包括打破时空限制、传播介质丰富、主体平等多元、主动选择性强等;同时,目前的技术还难以支持虚拟空间完全映射、复制现实世界的活动。因此,在虚拟世界中简单复刻现实世界的教学、互动方式,通常都难以达到同等效果。例如,有学者通过调查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状况就发现,线上教学总体上沿袭了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线上教学比传统教学效果差”这一看法在师生群体中还略占上风[58]。可见,必须开发基于虚拟环境或混合环境的新教学方式和互动方式,例如,在教学上,充分利用虚拟环境多介质、跨时空的交互特点,将教学置于多种仿真情境中,开展活动式教学,增强学生的可视化体验;在人际互动中,允许学生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自主选择与自身兴趣、人格等更匹配的多元交互对象,构成更加适应个人需要的虚拟学习共同体。最后,不仅要重视数字化职教空间的建设和使用,还要通过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以及用户反馈数据,不断发现空间建设中的问题以及师生的新需求,并据此进行空间优化、调试以及再设计,确保职业教育空间建设遵循用户导向、实用导向而非技术导向、政策导向。(三)核心架构:技术驱动组织治理变革,实现多元协同平台化治理数字化治理既是手段,为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更是目的,最终助推职业教育全息开放、永续发展的健康新生态的重塑。职业教育的平台化组织治理转型既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支持条件,又是实现职业教育有效治理的重要保证。数字化转型与职业教育组织的平台化治理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协调进程。然而,目前后者的进度远远落后于前者,这或将构成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职业教育治理变革的前提是理念变革,只有每个人的理念得到充分更新,组织形态和活动方式的变革才能最终得以落实。目前,职业院校行政、后勤和教学人员普遍存在对数字化转型不关心、不了解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有必要开展相关的宣讲与培训,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数字化转型,特别是要让人们意识到,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新技术的应用,更是职业教育活动方式的全面变革,与每个人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同时,新公共管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已经深刻改变了企业、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形成了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的大趋势,要以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加快职业教育行政领导干部的观念转变,改变经验治校、威权治校、官僚治校等思维。职业教育治理变革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进组织业务虚拟化和组织形态平台化。数字技术创造了与现实空间融合交互的虚拟空间,电子信号能够代替言语、纸张等成为信息载体。职业院校要充分利用安全、便捷、低成本、高时效的数据流动方式,开发并整合各类业务系统,推进学校日常业务的虚拟化,特别要在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的教务系统、学生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财务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系统间的接口统一和数据链接,逐渐形成统一的学校通用业务大平台,实现各部门各系统在功能上关联、在信息上互联、在业务流程上串联,推进院校组织功能的平台化整合。而在组织形态方面,学校业务的虚拟化平台化要求学校组织机构随之进行调整,打破科层制条块分割、官僚主义的症结,推进部门的整合化、权力层级的扁平化、决策权力的分散化下沉化,使职业院校具备组织形态简洁灵活、治理方式民主科学、人际关系平等和谐的特点。职业教育治理变革还要吸纳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同参与治理。开放与跨界是职业教育的显著特征[59],这使得职业教育始终伴随着学生、教师、管理者、政府、企业、社会大众等多元利益相关者,他们理应享有对职业教育的参与权、监督权。职业教育平台化治理,为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教育治理提供了条件,不同主体都可以经由互联网参与职业教育组织治理,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获取职业教育活动数据,并为职业教育事务建言献策;而职业教育组织要着力推进组织业务的公开透明、决策方式的民主参与、意见渠道的多元畅通、互动数据的共享开放。在此基础上,职业教育的社会支持程度将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治理也将具有更加民主化、开放化、多元化、科学化的价值底色。参考文献[1]马陆亭.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教育强国[J].上海教育,2022(36):1.[2]米加宁,章昌平,李大宇,等.“数字空间”政府及其研究纲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政府形态变革[J].公共管理学报,2020(1):1-17+168.[3]黄静.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5(13):17-20.[4][18]张青山.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11):59-63.[5][17]朱德全,熊晴.数字化转型如何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34(4):12-20.[6][25]王敬杰.新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困境与路径[J].职教论坛,2022(9):5-12.[7]伍慧萍.德国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项目布局与效果评估[J].外国教育研究,2021(4):76-88.[8]唐晓彤.俄罗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措施与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9):64-71.[9]陈川,胡国勇.日本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与启示[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2(11):30-39.[10]焦晨东,黄巨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类型及其启示--来自美、德、澳三国的多案例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33):11-21+29.[11][49]陆宇正,汤霓.数字化时代新基建重塑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挑战与因应[J].职教论坛,2022(8):5-14.[12][39][47][53]韩锡斌,杨成明,周潜.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现状、问题与对策[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2(11):3-11.[13]韩冰,顾京.浅析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现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6):14-16.[14]方绪军,施渊吉,梁晨.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课程转型:理据、风险与辩证[J].职教论坛,2022(10):50-58.[15]邹宏秋,许嘉扬.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三教”改革的政策理路与实践进路[J].中国高教研究,2022(6):103-108.[16]霍丽娟.数字化转型时代职业教育学习空间设计的理念、框架及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21(10):25-31.[19][22]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10(4):132-150+223.[20]THORNTON P H,OCASIO W,GREENWOOD C,et al.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C].London:SAGEPublications Ltd,2008:99-129.[21]DUNN M B,JONES C.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institutional pluralism:the contestation of care and science logics in medical education,1967-2005[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10(1):114-149.[23][31]朱成晨,闫广芬.精神与逻辑:职业教育的技术理性与跨界思维[J].教育研究,2020(7):109-122.[24]舒杭,顾小清.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基础与行动框架[J].现代教育技术,2022(11):24-33.[26][27][28]祝智庭,胡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探析与研究展望[J].中国电化教育,2022(4):1-8+25.[29]谢卫红,林培望,李忠顺,等.数字化创新:内涵特征、价值创造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9):19-31.[30]李锋,顾小清,程亮,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逻辑、内驱动力与推进路径[J].开放教育研究,2022(4):93-101.[32]马君,张苗怡.从职业知识到技术知识:职业教育知识观的逻辑转向[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44-154.[33]邹红军.数字化时代的空间流变与教育的家庭向度[J].南京社会科学,2022(2):148-156.[34]WACQUANT L D.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J].Sociological Theory,1989(7):26-63.[35]褚乐阳,陈卫东,谭悦,等.虚实共生:数字孪生(DT)技术及其教育应用前瞻--兼论泛在智慧学习空间的重构[J].远程教育杂志,2019(5):3-12.[36][48]袁振国.数字化转型视野下的教育治理[J].中国教育学刊,2022(8):1-6+18.[37]蔡跃洲,马文君.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64-83.[38]祝士明,张慕文.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动因、价值与路径[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2(9):3-12.[40]杨欣.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利弊及其调适[J].中国电化教育,2022(11):45-52.[41]CIBORRA C U.The platform organization:recombining strategies,structures,and surprises[J].Organization Science,1996(2):103-118.[42]王凤彬,王骁鹏,张驰.超模块平台组织结构与客制化创业支持--基于海尔向平台组织转型的嵌入式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9(2):121-150+199-200.[43]宋锴业.中国平台组织发展与政府组织转型--基于政务平台运作的分析[J].管理世界,2020(11):172-194.[44]姬德强.平台化治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国家治理新范式[J].新闻与写作,2021(4):20-25.[45]陈水生.数字时代平台治理的运作逻辑:以上海“一网统管”为例[J].电子政务,2021(8):2-14.[46]姜美玲.教育公共治理:内涵、特征与模式[J].全球教育展望,2009(5):39-46.[50]逯行,朱陶,徐晶晶,等.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基本问题与趋势[J].现代教育技术,2021(12):61-68.[51]祝智庭,许秋璇,吴永和.教育信息化新基建标准需求与行动建议[J].中国远程教育,2021(10):1-11,76.[52][54][55]胡姣,彭红超,祝智庭.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5):72-81.[56]欧阳恩剑.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变迁--制度供给理论的视角[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13):5-12.[57]刘晓.职业教育本质的再审视[J].职教论坛,2010(10):8-11.[58]邬大光,李文.我国高校大规模线上教学的阶段性特征--基于对学生、教师、教务人员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7):1-30.[59]张翌鸣,张园园.论职业教育的开放及跨界属性[J].职教论坛,2015(16):15-19.